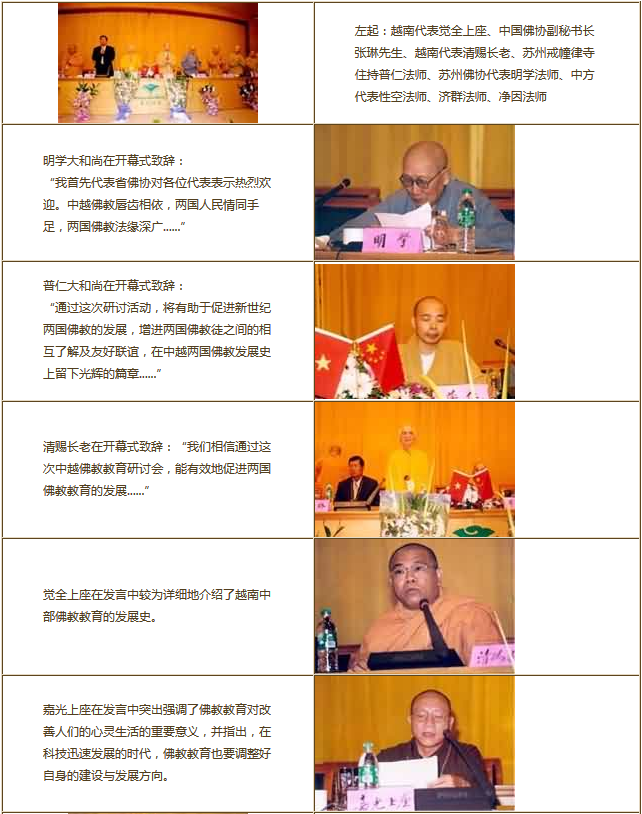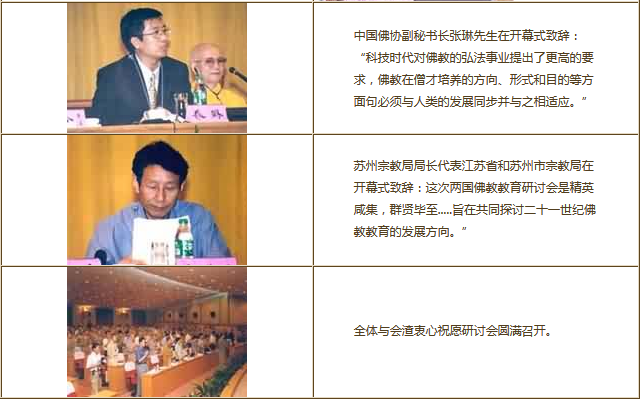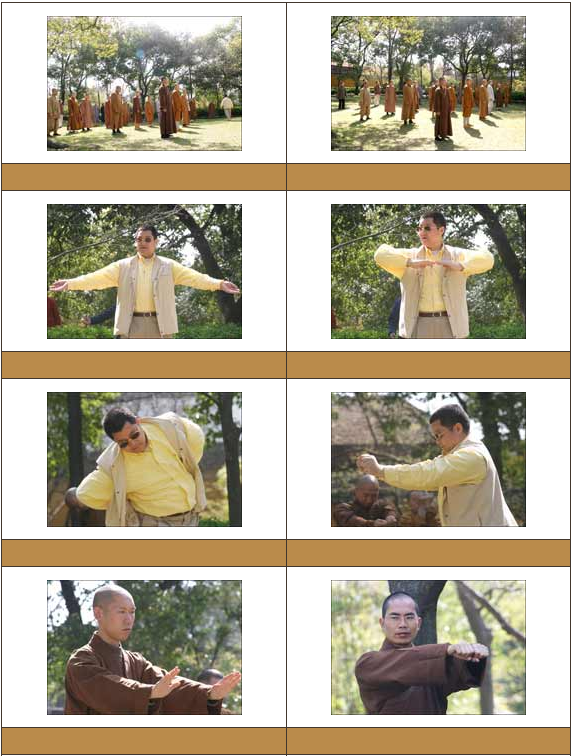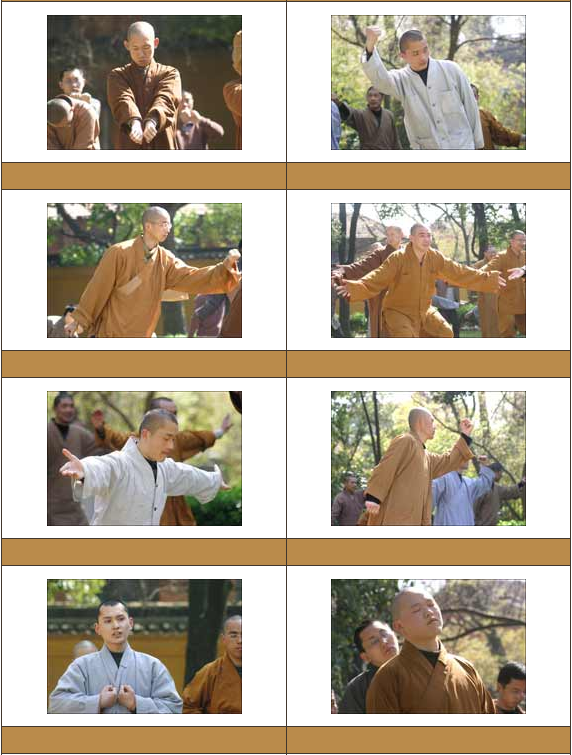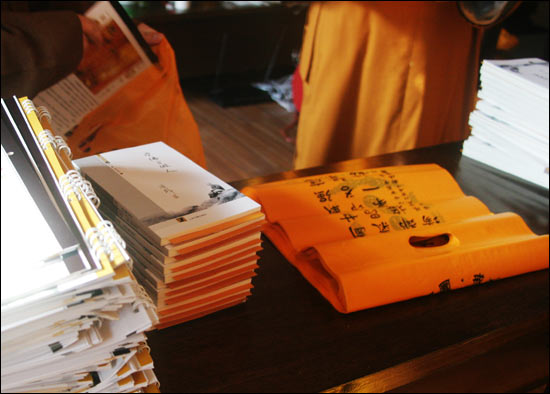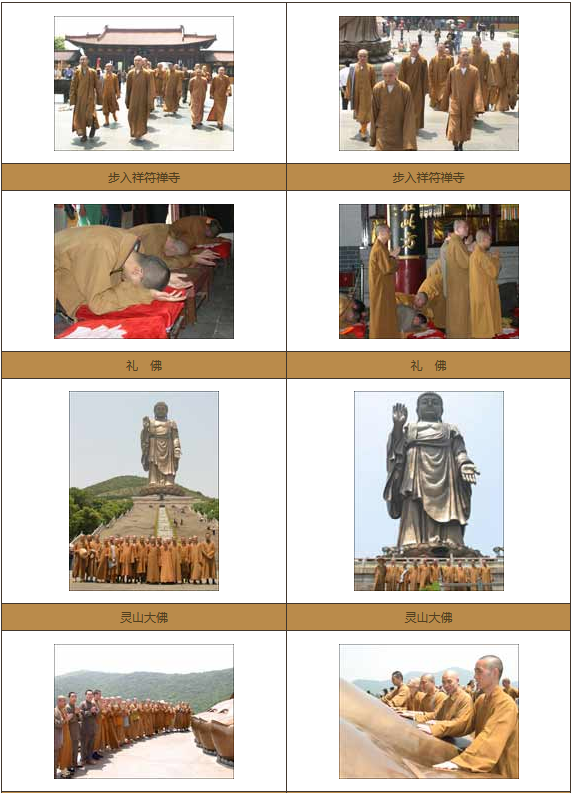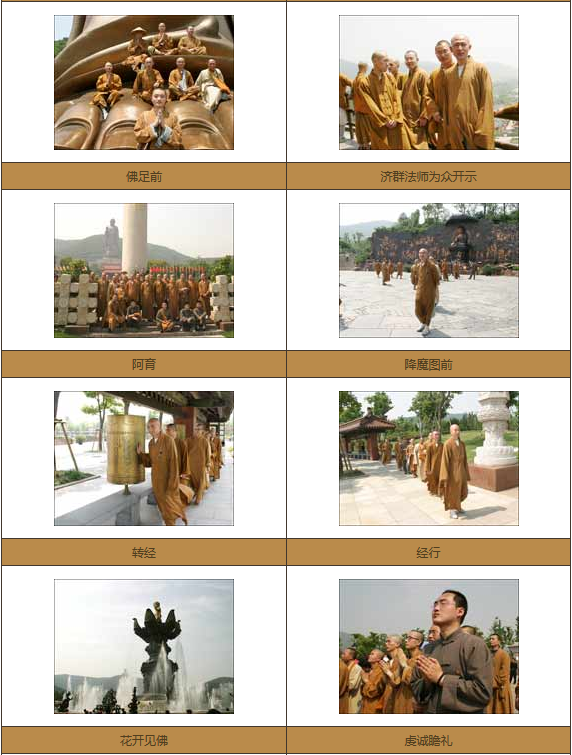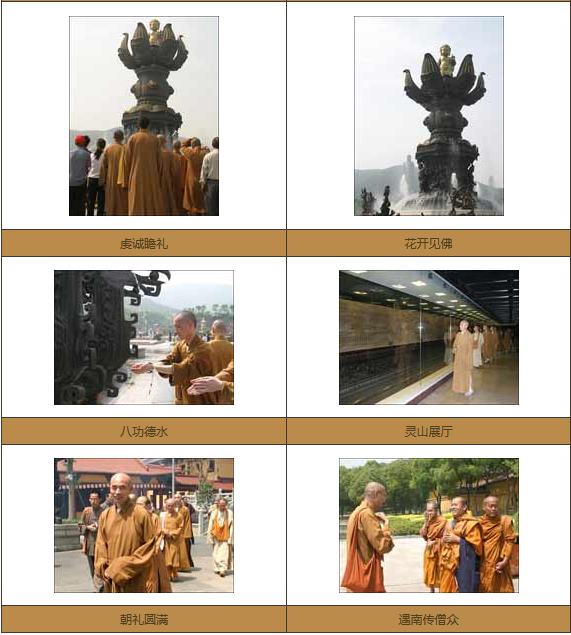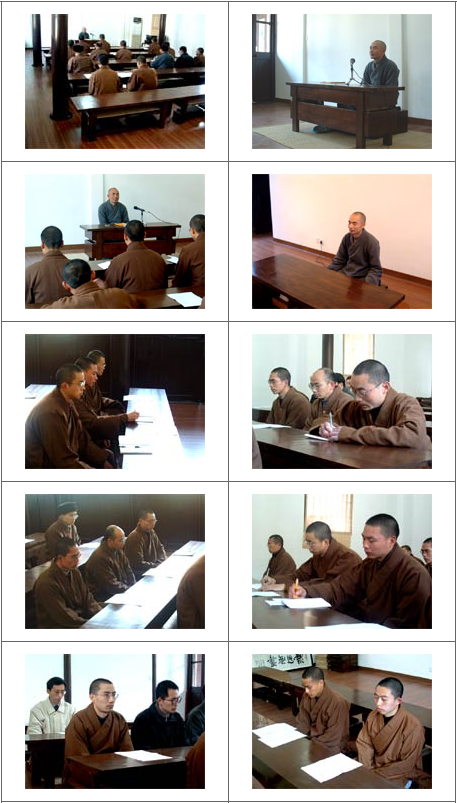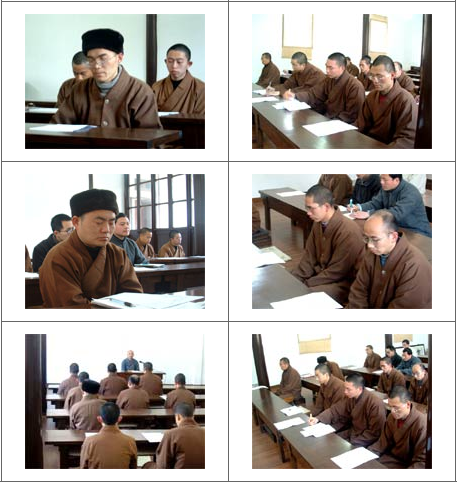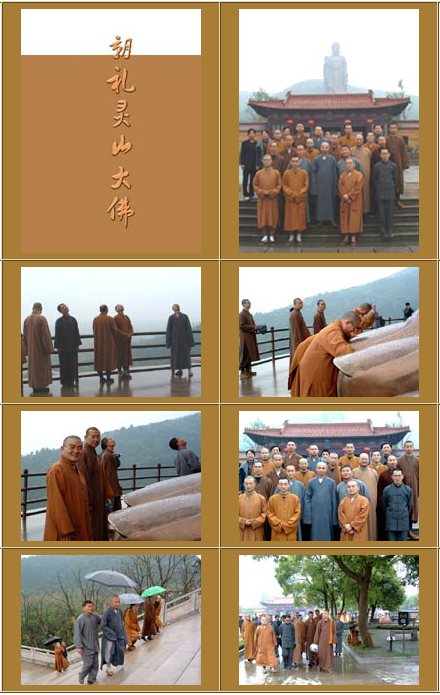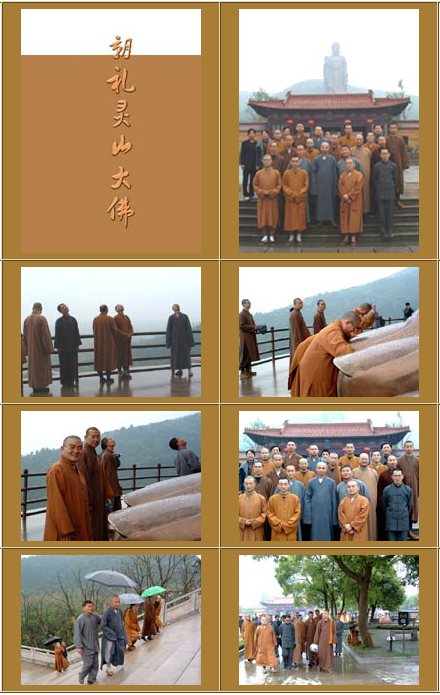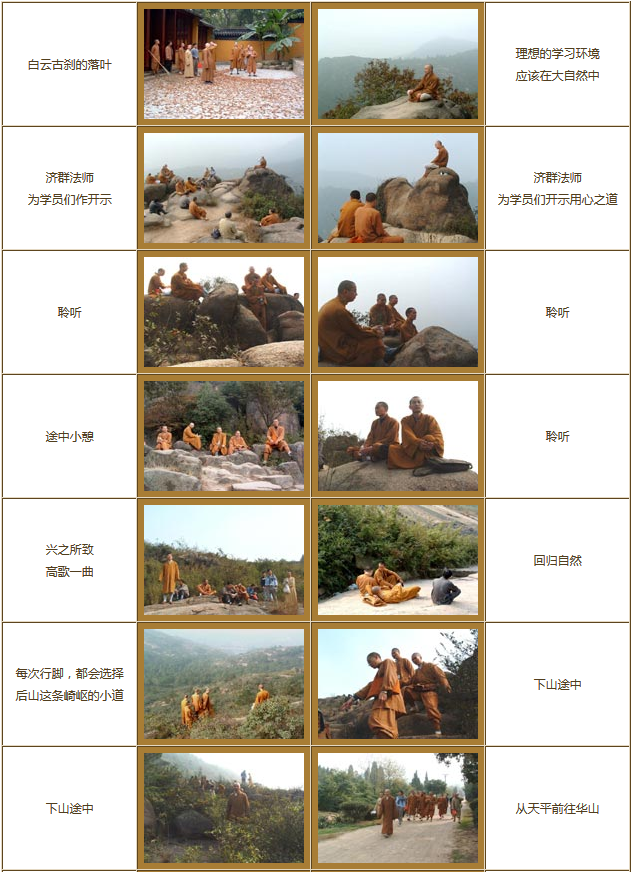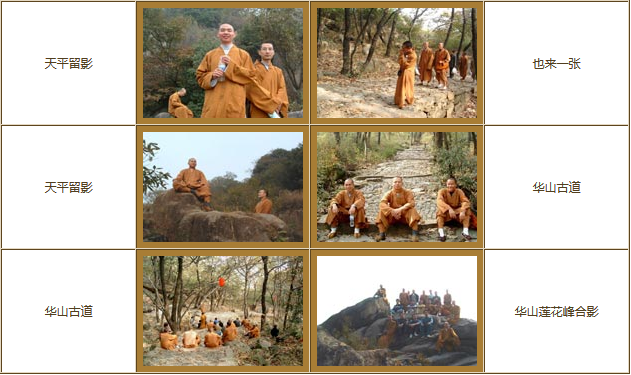2000年3月6日至7日,苏州西园寺隆重举行佛教教育研讨会,来自全国佛教界的法师居士及学术界的专家学者40余人参加了会议。
在开幕式上,西园寺住持普仁法师、苏州市宗教事务局席学明局长分别致欢迎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杨曾文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赖永海教授分别代表学术界、西园寺戒幢佛学研究所导师致词。在随后的五场研讨中,与会的20多位法师居士、专家学者先后发言,共同探讨21世纪的佛教教育。
西园寺戒幢佛学研究所副所长济群法师作了《我理想中的僧教育》的基调发言。他指出,佛教教育不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传授,而是在传授做人的方法。在我国当前全民关心教育,提倡素质教育、科教兴国的大背景下,佛教教育应向素质教育回归。要结合现实社会人生,解决自身生命的问题,关怀社会大众,培养具有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佛教专业人才。要以学佛做人为旨归、学术研究为工具,将佛法融入生活。为此,济群法师就戒幢佛学研究所办所方向提出了三个具体要求:第一要对佛学知识有全面的了解,第二要养成佛法的正见,第三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戒幢佛学研究所副所长净因法师作了《从对传统办学指导思想之反思谈佛教教育的未来》的基调发言。他首先厘清了佛教、佛法、佛学和学佛四者的关系,提出了研究所办学的新思维,提出要突破民国以来过于强调传统八宗在教学课程中的地位的佛教教育模式,主张以课题研究带动办学。他认为,不仅要向所有学有专长的佛教学者虚心请教,积极吸收佛教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还要在戒幢佛学研究所树立富有特色的严谨学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讨佛法的真谛。净因法师还强调了由知到信、由解到行的重要性,真正做到学修一体化。
戒幢佛学研究所导师圆慈法师在发言中指出,汉地佛教教育之不足,一是文献和外语教育不够,一是对世界佛教研究成果缺乏了解,从而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上海佛学院光慧法师对二十年来佛学院的历史作了回顾,探讨了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的佛教教育模式。福建种德(尼众)佛学院宏律法师作《僧教育漫谈》,希望能编制有针对性、有层次、有系统的教材,使初、中、高级佛教院校能有程序地接轨运作。她认为应致力于创办一所正规的佛教大学,分设管理学系、教理学系、教仪学系、艺术学系、外语学系、医药学系等。湖北黄石正慈法师作了《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造就一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僧才队伍》的发言,强调要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不拘一格选人才、用人才。
这次与会的学者不少,多是从事佛学研究的专家,故而对21世纪的佛教教育尤为关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杨曾文教授从北传佛教的特色,谈到当代佛教教育,认为在实践中要坚持以下四点:一、既重继承、又重创造的理论传统;二、包容大小乘、兼弘八宗、贯通内外的博大融会的精神;三、悲智双运、济世利生的菩萨之道;四、“不变随缘”的“智巧”。留日的陈继东博士通过祇洹精舍的建立,探讨了晚清中国佛教教育兴起的背景,阐述了与现代佛教教育的历史联系。北京大学李四龙博士回顾了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的办学历史,对佛教教育的课程设置和学制管理进行了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夏年先生介绍了王恩洋的教育思想,认为他的教育主旨是“儒佛为宗”,儒学是做人之本,佛学是认识世界之源,两者各有所重,互相渗透。武汉大学宫哲兵先生回顾了武昌佛学院的历史,提出了重建中应遵循的教育思想和管理方法。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张化平处长作了《关于新世纪佛教教育事业发展的思考》的发言,认为中国佛教教育的历史经验是当前佛教教育的宝贵财富,提出要以“人间佛教”为核心,形成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佛教教育思想体系。苏州大学潘桂明教授在《佛教教育的几点意见》中,对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办学方针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认为要处理好学术和信仰的关系,配合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佛教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唐明邦教授作了题为《巍隆大道,恢弘如来家业》的发言,认为要珍惜佛教教育的良机,发扬传统佛教教育的优点,完善佛教新式教育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韩廷杰先生提出,要学习中国佛学院办学的五条成功经验,做好西园寺的佛教教育工作。《法音》杂志社的居士分析了当前佛教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为应推行素质教育和全方位教育,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进体制、加强管理,才能在21世纪开创中国佛教教育的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广 教授在发言中强调,佛教教育的方向应该关心社会、联系社会。南京大学杨维中先生从宗教对话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佛教教育面向世界的必要性。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陈永革先生通过晚明四大高僧的学习经历,探讨了晚明佛教教育的两种模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夏金华先生从教育的目的、类别和方法等诸方面,比较了孔子和佛陀的教育观。上海社会科学院刘元春先生对当前佛教教育的定位、管理等问题作了认真的探讨,认为佛学院学生要经历受学、弘法和体证的三个阶段。杭州商学院王仲尧先生以《佛教和现代科学》为题,对佛教中“苦”、“般若”、“业”、“涅槃”的理论作了新的阐释。北京大学陈明博士在《古印度佛教医学教育略论》中对印度古代佛教的医方明作了独到的论述。
由一座寺院举办全国性佛教教育学术研讨会,这在大陆还是第一次。在闭幕式上,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传印法师、闽南佛学院教务长浩宇法师、上海佛学院教务长光慧法师、九华山佛学院藏学法师、种德佛学院宏律法师分别交流了他们参加会议的感受,对西园寺成功举办这样一次较高规格的佛教教育研讨会表示衷心的赞叹。一些专家学者还对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杨曾文教授提议创办一份高水准的所刊,北京大学白化文教授对研究所图书馆的编目、档案室的规范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等。最后,戒幢佛学研究所导师湛如法师作总结发言,认为通过以上诸多方面的讨论,这次会议基本上形成了以下两个共识:
1、佛教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合格的佛教专业人才,他们既要准确地掌握佛教的基本知识,又要具备高尚的宗教情操。
2、今后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佛教界和学术界的合作,为佛教研究提供可靠的保证,实现教学关系的“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