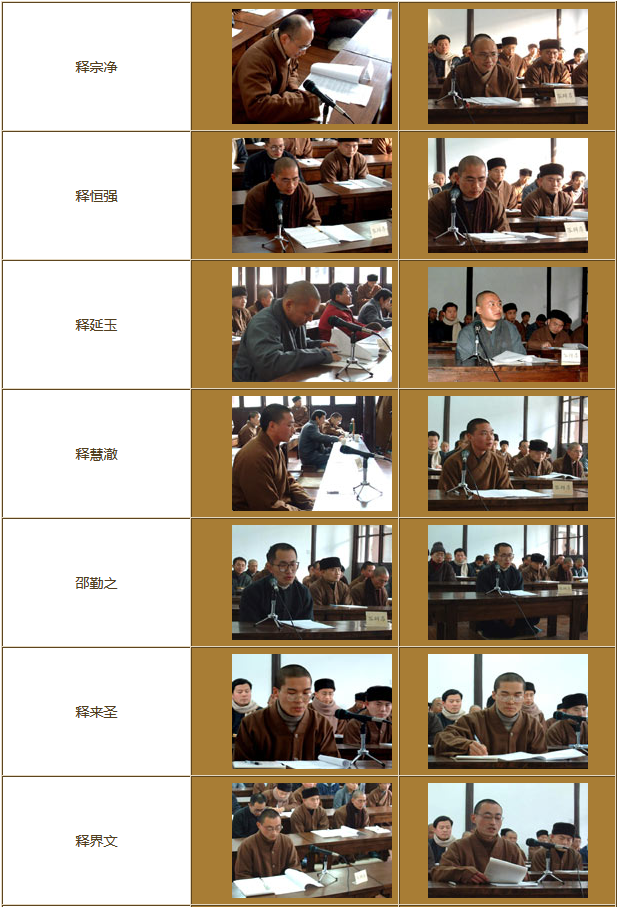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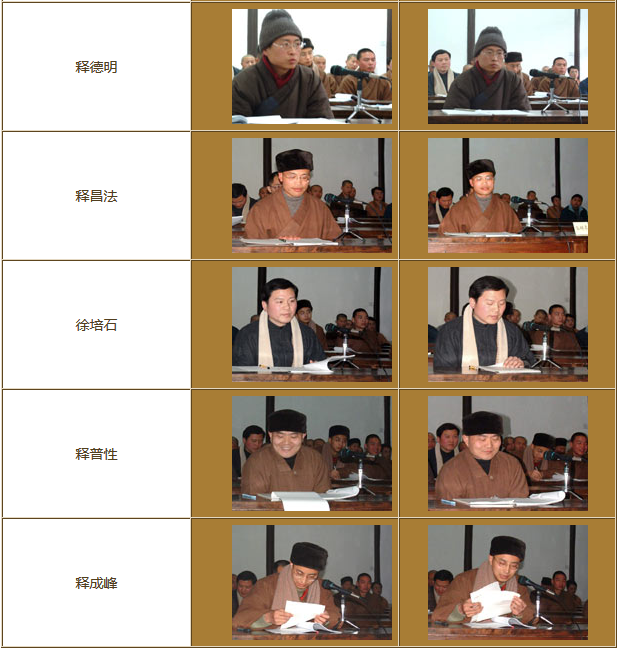

佚名
本来,佛经的偈颂是能歌唱的,但译成汉语后就不能歌唱了。这是因为:“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音无传。”(梁慧咬《高僧传》卷一五)
在佛教东传不久,便有人用印度的声律制成曲调来歌唱汉文的偈颂。“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四。至于本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四。”(同上)所以,六朝时代“转读”和歌唱梵呗颇为盛行,并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在当时的佛教道场转读经文极讲究转读的腔调: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不声,则俗情无以得入。
(《高僧传·经师篇总论》)
不仅如此,六朝的转读僧人还应精通教义和音律: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间起掷荡举,游飞却转,反
叠娇弄,动韵则榆靡弗穷;张喉则变态无尽。
(《高僧传·经师篇总论》)
只有这样,才能:炳发八音,光扬七善。壮而不猛,凝而不滞,弱而不野,刚而不锐,清而不扰,浊而不蔽,淳足以起畅微言,怡养神性。(《高僧传.经师篇总论》)
收到“听音可以娱耳,聆语可以开襟”的宗教与审美的效果。这是中国佛教徒对佛教音乐功能性的认识,既然佛教音乐的目的是“宣唱教理,开导众心”,是“集众行香,取其静摄专仰也”,这就决定了佛教的音乐美学观念:以静、远、肃穆、平和为高,而反对“淫音”“荡调“娇弄颇繁”。
南北朝的唱导,也是一种说唱兼有、声文并茂的讲演艺术。所谓“唱导”,《高僧传》说;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
唱导主要以歌唱事缘、杂引譬喻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这种做法魏晋时已很盛行,但尚无一定规矩,至庐山慧远“躬为导首”,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揖、广弘佛法的途径,“遂成永则”,自东晋始确立了唱导制度,为后世佛教音乐的目的、内容、形式、场合的规范奠定了基础。
从唱导的内容与效果看,《高僧传》中有一段描述: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布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往业,覆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合酸。于是阂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
唱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教、宣传法理,但枯燥的义理宣说较难吸引听众,因此,不得不在“无常”、“地狱”、“昔因”、“怕乐”、“哀戚”等方面加以艺术上的渲染夸张,自然取得较好的效果。
南北朝时涌现出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县宗、道慧、僧辩等,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
“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其见闻者,莫不惊异。
梁武帝萧衍,写信佛教,也精通音律。《隋书·音乐志》说他亲“制《善哉》、《神王》、《大乐》、《大欢》、《天道》、《仙道》、《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
名为正乐,皆述佛法”。此外,他还让“童子倚歌梵呗”,开
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子伎”。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盂兰盆会”、“梁皇宝仟”等佛教典仪,为佛教音乐提 供了新的形式范例和演出场合。
编辑:杨杰
蔡惠明
佛教音乐是伴随着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我国的。最初由于与中原地区的语言及音乐传统不适应,未能流传。后来经僧人们长期摸索和实践,逐渐地熔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宗教音乐于一炉,形成了以“远、虚、淡、静”为特征的佛教音乐,并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一部分。
北魏时佛寺众多,“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屠音”就是“浮屠之音”,佛教音乐开始普遍流传。隋代宫廷的“七部乐”和“九部乐”中的天竺、安息、龟兹等乐,皆来自佛教国家。
南齐肖子良曾“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这是佛教音乐的起源。梁武帝执政后,亲制《善哉》、《灭过恶》、《断苦轮》等十首歌词,配曲谱演唱。
到了唐代,增加高昌乐成“十部乐”,并用铙、钹、钟、磬等法器伴奏。
净土宗名僧少康制“偈”、“赞”等,增添了宗教内容,留传至今。近年北京成立佛教音乐团到法国、德国、瑞士等国演出,风靡了西欧。
1990年为纪念弘一法师(李叔同)诞辰110周年,还编印了由他题词、谱曲的歌曲集,录制磁带,举行专场演出。
编辑:杨杰
佚名
佛教音乐源于印度,中国汉地佛曲的发展,是由梵呗开始的。梵,是印度语“清净”的意思。四是印度语“呗匿”的略称,义为赞颂或歌咏。中国的梵四音乐,是模仿印度的曲调创为新声,用汉语来歌唱。
自佛教传入至三国时,来自印度、西域的一些高僧在汉地传播、翻译佛经的同时,也带来了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月氏人支谦据《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成《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亦曾制此曲,又传《泥洹呗声》。此外,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的帛尸黎密多罗也是西域人;月氏人支县南“裁制新声,梵响清美”,传“六言梵呗”于后世。“原夫经震旦,夹译汉庭。北则些(法)兰,始直声而宣剖;南惟(康)僧会,扬曲韵以讽通。”(宋赞宁《宋高僧传》)则把竺法兰、康僧会奉为北、南两派赞呗的祖师。他们所传梵四,应该是西域风格的佛曲。然而,这些异国风味的“胡呗”并没有广泛流传开来。
中国化佛曲的创始者应该是三国陈思王曹植。相传,曹植“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乃慕其音,写为梵呗”(《法苑珠林》卷三四),曹植的“改梵为秦”,就是在梵音的基础上有所创作,“创声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梁慧皎《高僧传》卷一五)。一契便是一个曲调,四十二契便是四十二个曲调联奏。这种“鱼山呗”已经出现了与印度佛曲相异的形式,代表了佛曲华化的趋势。
《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卷七七八年)载有齐王融《法寿乐歌》十二首,每首均五言八句,内容歌颂释迦一生事迹,从其歌辞体制来看,无疑是用这种华声梵四来歌唱的。
编辑:杨杰
田青
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佛曲随佛教传入中国后,也经历了大体相同的过程。中国佛教音乐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级:一、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二、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北及多样化阶段;三、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四、宋元以降直至近代的通俗化及衰微阶段。
唐代,佛曲大盛,俗讲风行,朝庭耽于佛曲,百姓则把庙会视为最重要的娱乐场所。无论寺院、宫庭、民间、佛教音乐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寺院内,净土宗的流行为佛曲的传播与宗教活动中音乐的大量使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初唐善导,传净土法门,但专心念佛,曾著《法事赞》、《往生赞》、《般舟赞》等歌赞三卷。中唐法照,制定“五会念佛”法规,并作有《散花乐》等曲,影响甚远,流传至今的《千声佛》等绕佛之曲,可视为“五会”之遗续。晚唐少康,则更辟蹊径,面向民间,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新的佛曲。赞宁《高僧传》中称:“康所述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得处中曲韵。”用当时、当地老百姓所熟悉喜爱的音调演唱佛曲,应该说是中中国佛教音乐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宫庭,来自西藏佛国的音乐,成了当时上层人士的“流行音乐”。在隋七部乐、九部乐及唐九部乐、十部乐中,都有大量佛曲。佛教音乐与燕乐大曲中龟兹乐、天竺乐的关系,尤为密切。在《隋书·音乐志》中《羯鼓录》、《唐会要》、陈《乐书》中,均载有大量唐代佛曲名。曲梁乐演化而成的“法曲”,经隋至唐,成为宫庭音乐中极富特色的部分。天宝十三年(754),唐玄宗李隆基命刻石太常,改诸佛曲调名为有道教意味的汉名,如《龟兹佛曲》改为《金华洞真》等。此举虽是唐玄宗抑佛扬道的一个政治行动,但也从反面说明唐宫庭音乐中佛教音乐的地位已严重威胁了“正统”音乐的地位。唐懿宗时,佛诞之日,“于宫中结彩为寺”,宫庭音乐家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作菩萨蛮舞,如佛诞生”,整个宫庭,似乎都变成了节日的寺庙。
在民间,佛教音乐也成了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姚合“仍闻开讲日,湖上少渔船;,“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以及韩愈“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的诗句,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佛教俗讲僧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他们不但在岁时节日举行俗讲,并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念经,且有化俗法师不殚劳苦,游行村落,以最通俗的形式劝善化恶。甚至约集庙会,赏花唱戏,使唐代的众多寺院,实际上成了社会的主要娱乐场所。钱易《南部新书》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寺),小者在青龙(寺)。其次荐福(寺)、永寿(寺)。尼讲盛有保唐(寺),名德聚于安国(寺),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寺)。”艺僧们高超的音乐技艺,不但征服了众多善男信女的心,甚至使当时第一流的宫庭音乐家也为之倾倒。据说贞观年间长安庄严寺的艺僧段善本,曾使“宫中第一手”的琵琶大师康昆仑拜而称弟;长庆中,俗讲僧文溆则不但使“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且令宫庭音乐家黄米饭折服,“依其念《四声观世音菩萨》”而撰成名曲《文溆子》。敦煌所传大量俗讲底本“变文”和“曲子辞”,以及琵琶曲谱等文物,皆为唐时佛乐繁盛的有力佐证。
宋元以后,佛教音乐因市民阶层的出现而日趋通俗化并从多方面影响了中国说唱音乐及器乐演奏的发展。从现存宋词和元曲的词、曲牌中,均可见到佛教影响的深刻遗痕,如词牌《菩萨蛮》、曲牌《双调五供养》等,甚至在文人士大夫的七弦琴音乐中,也出现了《普庵咒》这样的曲目。吴曾《能改斋漫录》说:“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赞。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拨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唱道之辞”,从中可窥见宋代佛教徒吸收民间音乐甚至道教音乐以丰富自身的情景。继唐代俗讲而起的宝卷,在宋时盛极一时并一直绵延到明清,影响了近世多种戏曲及曲艺音乐。如《金瓶梅》七十四回“吴月娘听宣王氏卷”中便记载了比丘尼在市民家中宣讲宝卷的详情,其所唱除偈、诵、讲之外,还有《一封书》、《楚江秋》、《山坡羊》、《皂罗袍》等时曲,可视为明代佛曲深入民间、成为市民音乐生活重要内容的生动例证。元代,曾一度失传的“瑜伽施食焰口”随密宗的复兴而再度流传,经后世的增益演变而逐渐形成今世尚存的一套融赞、偈、咒、器乐、手印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炉,带有一定情节性的佛乐套曲。
明清之际,佛曲愈发通俗化并日益深入民间,许多佛曲用民间曲调演唱,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五年(1418)颁布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通令全国佛教徒习唱,其中大部分曲调为当时流行之南北曲,如《感天人》之曲即《小梁州》、《成就意》之曲即《好事近》等。只惜此书有词无谱,且未能流传。从明清到近代,佛教音乐与唐宋时相比,从整体上看是日趋衰微了,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衰微的同时,由于佛教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尤其是民间器乐和说唱音乐)却日趋繁荣。因此,佛教音乐衰微的过程,也可以视为一个与民间音乐进一步融合的过程。
编辑:杨杰
佚名
一、佛乐种类
佛教音乐通常分为佛事音乐和以佛教题材为主题的或由佛事音乐改编的通俗音乐。这里仅介绍佛事音乐的种类:
1.朝暮课诵:
每天早、晚两次,其形式与程序基本相同,内容各异。早课的内容与程序为:诵《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心经》(每月初一、十五之前加唱《宝鼎赞》)、唱《回向赞》《赞佛偈》、绕念佛号、唱《发愿偈》、三皈依、诵《大吉祥天女咒》、唱《韦驮赞》。晚课的内容和程序为:诵《阿弥陀经》(或《大忏海文》)、蒙山施食、唱《回向偈》、《赞佛偈》、绕念佛号、唱《发愿偈》、三皈依、唱《伽蓝赞》。
2.祝圣佛事:
这类佛事主要是佛菩萨圣诞的庆祝活动,包括佛的诞生日、出家日、成道日、涅槃日,菩萨的诞生日、出家日、成道日,及祖师圆寂纪念日等。如每年夏历四月初八日为“浴佛节”,即为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诞生。据佛经记载,此日佛陀“生时龙喷香雨浴佛身”,因此后来佛教四众弟子在纪念佛陀诞辰时亦以各种香水灌洗佛像。浴佛仪式的程序分为八项:(1)集合僧众;(2)迎请佛像;(以上两项没有唱念,只有礼拜。)(3)将佛像请回,唱《稽首皈依大觉尊》;(4)将佛像安置于佛座,然后以香水灌沐,唱《沐浴真言》、《释迦大赞》;(5)主法者敬致诵词;(6)祝圣绕佛,唱《佛宝赞》、《赞佛偈》;(7)回向皈依,唱《回向偈》、三皈依;(8)圆满礼佛,唱《浴佛功德殊胜行》。
佛菩萨圣诞祝仪的格式、程序基本相同,只是所用“赞”有“六句赞”和“八句赞”的区别,而曲调则完全相同。以释迎牟尼圣诞祝仪为例:(1)唱“香赞”,即《戒定真香》;(2)念诵,包括“南无楞严会上佛菩萨”(三遍)、《楞严咒》、《心经》,唱“摩诃般若波罗密多”(三遍);(3)唱赞偈,有《佛宝赞》、《赞佛偈》;(4)绕念佛号;(5)拜愿;(6)三皈依。
3.普济佛事:
这类佛事是为现前之人忏悔业障、植福延龄,或为超荐先亡、救拔恶道众生而举行的。主要有:
(1)随课普佛:随早晚课诵加入赞偈、拜愿、宣疏文等,分延生普佛和往生普佛两种,此略。
(2)忏法:忏法有多种,如“净土忏”、“梁皇忏”、“千佛忏”等,此略。
(3)瑜伽焰口:简称“焰口”。通常用于超度亡灵,历时约四至六小时。程序为招请、结界、施食、施水、超度等项。以口中诵赞、偈、经文及密咒,心存观想并辅以手印,身口意三业加持。
(4)水陆法会:全称“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盛会”,简称“水陆”。是为超度普济水中、陆上一切鬼魂的大型法会,是各种佛事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佛事,少则七天,多则四十九天,参加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人、千人以上。设有内、外各种坛场,主要有诵经、礼忏、施食施水追荐亡灵等。水陆法会中大约有上百首曲调,有大量的散套曲牌。
二、佛乐形式
1.佛教器乐:
传统佛教器乐有南北流之分,各有不同特点。首先是乐器编制,北方的编制主要有鼓吹三大件笙、管、笛,以及云锣、鼓、铪子、木鱼、铛、铙、钹,南方编制在北方的基础上加箫、琵琶、弦子、胡琴,因此,北方称“吹打”或“鼓吹”,南方称“丝竹”。近代以来,较著名的寺院器乐有五台山的“鼓房”吹打乐和北京的寺院管乐,江南的“十番鼓”和“十番锣鼓”等。
2.佛教声乐:
佛教声乐可分为梵呗、渴、礼忏歌曲、诵经音乐和应赴音乐。
(1)梵呗:指一切梵音歌唱,主要有赞、祝延等。其中赞用于赞颂佛、法、僧三宝,体载分大赞、小赞。大赞有八句和十句之分,小赞只有一种体载的曲调,叫“六句赞。”而祝延(“祝延”本为吉庆辞语,意思是消灾吉祥、祝福延寿,后来以此命为梵呗名称。)仅有四首词曲,世称“四大祝延”,即《唵嘛呢叭咪吽》、《唵捺摩巴葛瓦帝》、《唵阿穆伽》、《皇帝万岁万万岁》。
(2)偈:一般四句或八句(也有更多句数的),每句字数相等。有四、五、六、七、八、九言,常用偈的言数一般为四、五、六、七言,类似我国古体诗。偈是佛事中重要的唱诵体载,其作用是对前面唱念内容的进一步阐发、补充和总结。按题材分有赞佛偈、发愿偈、警众偈、回向偈等。
(3)礼忏唱诵:即礼拜忏悔中的,主要用于圣诞祝仪、课诵普佛、忏法等佛事,最常见的有:《拜愿》和《三皈依》。
(4)诵经:指唱诵经文、密咒的曲调。其中密咒有《华严字母》、《普庵咒》和《音乐咒》等。
编辑:杨杰
佚名
——书之妙,神彩为上,形质次之
公元五世纪,王僧虔在《笔意赞、》中首次提出“神彩”论。所谓“神彩”,实际上是书法家流溢于笔墨点划之间的一种态度,或者说一种寄托在字里行间的精神状态;王僧虔的这种理论,也许从魏晋品藻人物风神而来,但与六朝绘画的“以形写神”似不同。形神论作为一种表现方法,是将一物象通过精熟的技法,“应物象形”充分地表现出自然物的神态和气韵,它强调的是客体、具体物象。“神彩”论的建立;强化了书法艺术的抽象意味,说明书法作为艺术所创造的不过是文人们利用这样的形式——书法的特殊空间——所表达的主体精神状态而已。
按郭若虚的看法,“气韵本乎游心”而“神彩生于用笔”,笔的运用,在于腕指而通于一心,是人格个性直接表现的枢纽,那些线条能以抽象的笔墨表现极具个性之人格风度及个性情感,并以自我深心的心灵节奏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笔法的生机,往往被解释为书法所产生的灵性意识的具体化。因为笔法的运用不是几何式的或机械式的,而是内在无限可”能性的投影,即它是最优雅的精确的灵性的表现,因为它表达“自己心中的韵律,所绘出的是心灵所直接领悟的物态天趣,造化与心灵的凝合”(宗白华《美学与意境》136页)。
禅宗在弘忍之后,声誉日隆,神秀的《观心论》,主张学者唯须观心,不必外修戒行及种种功德,这样的理论对于中国的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谓“得简易之道”的追求很可能由哲学中摆脱繁琐空洞的经义之学而感染到艺术上要求发生一种明快简捷的形式,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更为单纯的艺术创造。唐代张怀瓘的“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唯观神彩,不见字形”的理论,显然受到佛教禅宗的启示:深识书者,唯观神彩,不见字形,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何有不通?
这是一种非常大胆的理论,他要求对于书法有精深理解的人要对字形视而不见,以一种“异照”之心;即从某特殊的角度,直接感受到书法中蕴含的力量,因此,达到最高艺术境界的书法不仅据弃了“法”,而且是不能用语言采描述的。八世纪前后,真正能以心灵力量来进行书法艺术创造的艺术家,或者真正能“唯观神彩,不见字形”的书法家,大多数是佛教徒或与佛教有关的文人,这也许能够从另一角度证实神彩唯一论的提出是受了佛教禅宗的影响。
遵从书法神彩论的一大批僧人书法家在八、九世纪创造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被目为疯狂的僧人艺术家。
张旭的书法在公孙大娘剑舞的启示下,超越了笔墨技巧程式,线条中那仿佛走龙奔蛇、刚圆道劲、倏忽之间变化无常、急风骤雨般不可遏止的情态姿势,不正表明激烈旋转的剑器舞和书法中狂草在内在生命节奏的息息相通吗?“以狂继颠”的怀素,那孑奇万状、连绵不断、忽擒忽纵的结体布局,那电闪雷鸣、不可端倪、不可遏止的笔势,那笔止而意未尽、书停而韵未绝的意态,不正是“唯观神彩,不见字形”的显现吗?唐人的狂草把中国“线的艺术”推上了抒情的最高峰。张、怀的草书都是中国书史上自然美的无上杰作,透出的那不可一世的傲岸精神的文化背景,盛唐浪漫的激情、骨力和风气,更透出一种“禅气””——追求适意自然的境界。既然“本心即佛”,只要尊重自己的心就行了,一切外在的束缚和清规戒律都是多余的。这时的书法美学和书法创作都毫不含糊地追求“逸”的境界,亦即不拘常法、超凡脱俗、有韵外之旨的境界,一大批僧人书家如高闲、辩光、亚栖、梦龟、贯休……都在“无拘束”的草书里独抒性灵。
不管我们把“神彩”理解成事物的“精髓”也好,“本质”也好,它总是代表着那种不拘于形迹,忘形忘质,超越于有限之“形”的一种无限自由的境界。这样从心灵中流出的线条节奏是天然的。书法神彩论要求尚意而突破“法”的束缚,所谓得“简易”之道,就其风格来说是奇特的,而莫可楷模,这就决定了它的无法度、无具体物象的规范性。从苏东坡开始,北宋书法理论完成了从“法”向“意”,即从“神格”向“逸格”的转化过程。东坡的书论从庄禅而来,提倡一种美学追求,即反对矫柔造作,追求朴质无华、平淡自然。因此他认为张旭、怀素的狂草有一种迎合时尚,刻意求工、求妙的倾向,还有待于“物,”故未能尽妙。那比得上晋人钟舔、王羲之书法“萧然自有林下风:那一派潇散超脱、一任自然的风流逸韵,那才是真正的禅风、禅意的东西,这是为苏东坡极欣赏亦极仰慕的。
就禅宗来说也有狂禅与雅掸之分。北宋苏、黄、米在书法理论上所掀起的思潮是“呵祖骂佛”,反叛一切教条的狂禅思潮,到南宋末这股思潮便旋即低落了,以后的禅宗,狂的成份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以姜为代表的“雅”禅。他评王洽书时说;清逸闲雅,真不在右军下也。(《续书谱.草书》)
在姜夔的书论中,强调“清逸闲雅”、“风神”、“飘逸”,正是这种“雅”的禅风。与苏轼虽谈清空、疏淡,但难以泯灭个性的骚动的“狂禅”相比,显然带来禅境上的一些变化。那就是“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的神韵,那就是疏淡到没有火气方得高境,这就是姜葵的“萧散之气”的内在旨趣。这种尚雅的变化到了明代的董其昌那里便成了“淡雅”。尽管董其昌并没有在书论上划分“南北二宗”,但他在书论上倡导“淡”的禅境其实也倡导南宗的书法:余谓张旭之有怀素,犹董源之有巨然,衣钵相承,无复余恨,皆以平淡天真为旨。(《画禅室随笔跋自书》)
作书最要泯没棱痕,不使笔笔在纸素;成板刻样。东坡诗论书法云:“天真烂漫是吾师。”此一句丹髓也。(《画禅室随笔·论用笔》)
董其昌的“平淡天真“并非是对姜夔“雅”禅的简单继承,他要把这种“淡”的旨趣导向极点才心满意足。谈到极点,简到极点,就有极广阔而丰富的想象空间,就有本真所凝聚的“气韵生动”的自然之道显现。淡并非不绚烂,绚烂之极,乃造平淡。看似极淡的墨色,抽象、单纯却内蕴极为丰富的线条,成为表现艺术家自我生命的形式。“淡”成了书家由有限通向无限的桥梁。
明代李日华也喜以禅论书,他与董旨趣相近,曾盛赞黄庭坚:淡虑天真,惕然自得之语,书法清道超朗,知其胸不挂一尘也。(《六砚斋二笔》卷二)
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若是营营世念澡雪未尽,即日对丘壑,日摹妙迹,到头只是与髹采污墁之工争巧拙于毫厘也。(《紫桃轩杂缀》)
禅要求人“顿了本心清净”,影响书法创作则要求书家排除一切尘滓意念,追求空明澄净的境界。所以,“平淡天真”并不仅是一种人品、性情,更重要的是人的一种超然状态:超然于物外,摆脱羁累,去掉壁障,顺乎万物自然之性,而不加以人工矫饰之力的返朴归真。
近代僧人书法家弘一大师也谈到“放”与“淡”:世法唯恐不浓;出世法唯恐不淡。欲深入淡字法门,须将无始虚妄浓厚习气尽情放下,放至无可放处,淡性自然现前。淡性既现,三界津津有味境界如嚼蜡矣。(《寒笳集》)
要达到“淡”之境,必须空、舍、放。除一切荣辱、得失、穷达、尘滓,乃能空,空乃能淡。所谓舍者,是一念不生,万缘俱寂,胸无半点系累牵挂,乃能以舍入淡者,他认为唯有心中空无一物,有空灵澄澈的精神境界才能有“平淡天真”的风格。在这化境中,人生的确进入了天真而奇妙、淡泊而丰富的层次,这时你会享受到自然万象向你涌来的世界,体会到委身大化,无线无系的自由。透明的心境、真实的生命与透明的世界、自在自为的天地合一。书法家作为一个艺术家与禅僧作为一个彻悟者都要求精神上的完全解脱、要求人的本质生命与禅的形式完全契合,达到如此奇妙的境界,才能领略到书法作为艺术的真话。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说:
……由恬淡寂寞的人生所流露出的纯素之美。“纯素”是另一种语言表现,那是后来画家、画论家所常说的“逸格”或“平淡天真”。逸格和平淡天真之美始终成为中国绘画中最高的向往……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流。
编辑:杨杰
佚名
书法的形式来源于自然的意象。“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汉蔡邕《九势》)自然界中最简单的两条线:一(阴)、一(阳)早在《周易》时代,人们就赋予了它们以“刚”、“柔”特殊的生命力。“上”、“下”那是地平线上下生生不已的自然之物的宇宙概括。可见简单的线条,都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迹化。
书法作为艺术,象征、暗示着宇宙的本质,因而在最早的书法艺术文献中,总是将自然界中一些富于动态的事物来比拟。蔡邕的《笔论》:
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
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观乎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若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这些书法艺术家,几乎使用了他们所能观察到的一切自然物的运动形态,来与书法中的那些宛转反复的线条进行比拟,这说明了自然生命的形态、运动的本质最终都归结于、凝缩于、抽象化于那些隶书、草书、行书的线条中。
所以,宗白华认为,“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宗白华《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美学散步》83页)中国书法里的字,已不仅是表达概念的符号和工具,而是一个表现生命的结构和动作的单位。中国书法通过笔、墨、结构和章法,表现艺术家对宇宙及人生的理解。
线条的生命感,原本是线条自身固有的特性。因为它是人生命意识的一种抽象物,任何形态的线条(或直或曲),都积淀着人的某些意识和情感。笔势所含有的完整的生命,体现于种种的线条和笔法中,表达心中的韵律,所绘出的是心灵所直接领悟的物态天趣,造化与心灵的凝合。
这样一种“同自然之妙有”的空间,又是一个艺术上纯粹的空间,它由充斥宇宙万物全力所暗示或者说所组成。笔画线条之间,存在着力的纯粹关系,平衡、倾斜、夹持、扶助、打击、架抬、依靠等。然而这些关系又是不可估量的心理关系,生活中的一切体味、感叹,乃至心灵深处最微妙的颤动,都有可能通过敏感的艺术家气质的手指而贯注于柔软的笔毫间,流泻于洁白的绢纸上,而这些精妙的心灵的痕迹,又在后人“如见其人挥运之时”的想象中,获得新的生命。
人的生命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时间过程,也最纯粹地表现在书法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只有这样一种艺术中最抽象、最单纯的形式,其宛转翻复、充满了生命的动感的线条,才有可能如此简捷、深刻、富于想象力地体现着人的生命本质。
编辑:杨杰


 西园戒幢律寺
西园戒幢律寺
<微信服务号>
地址:苏州市留园路西园弄18号
电话:0512-65349545(客堂) 65511746(弘法部)
信箱:admin@jcedu.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