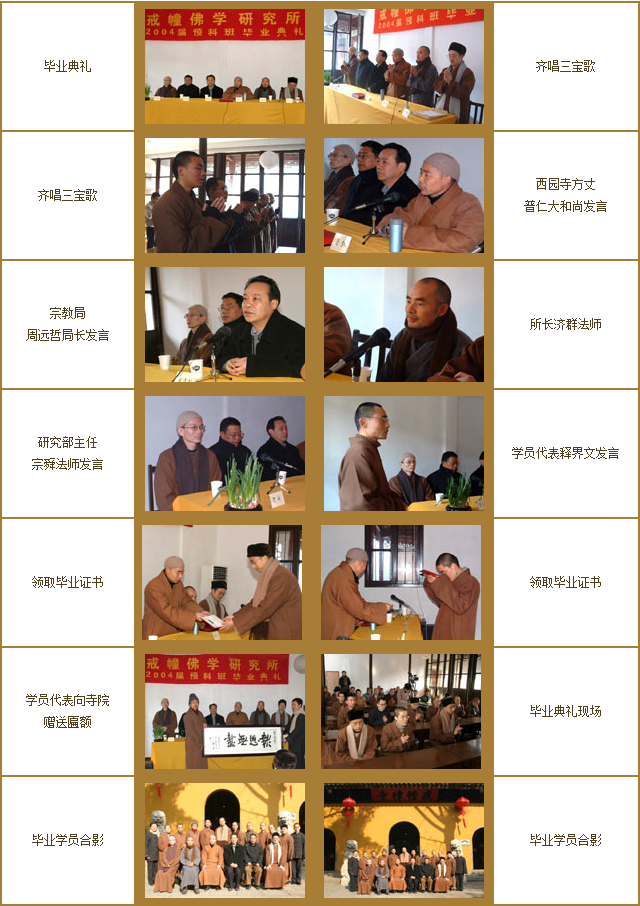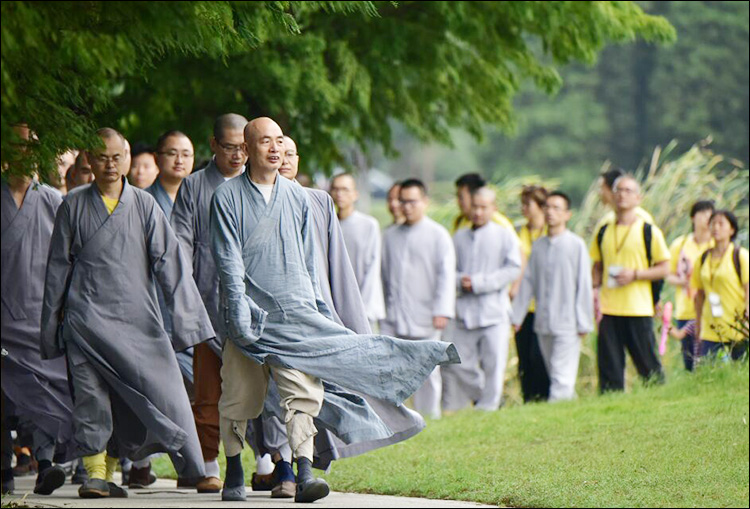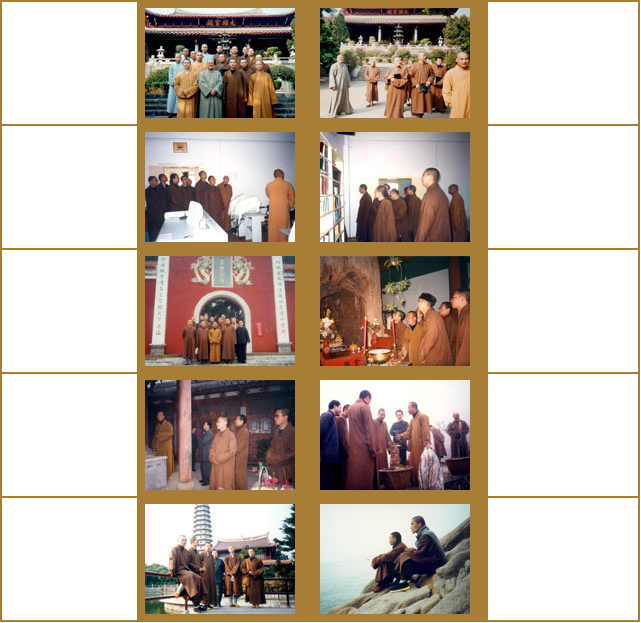本所教育依佛法的修学次第,以僧格养成、迈向解脱及成就佛陀品质为目标,下设僧伽教育部,完成本科时期的教育,成绩优秀者进入本所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学制及课程设置:
1、本科班,学制三年。培养对三宝的信心及养成僧格,以迈向解脱的教育为目的。培养闻思正见,掌握佛法基本要领和学修次第,修习止观,掌握弘法布教及寺院管理能力。
2、研究班,学制四年。注重菩提心的修学和菩萨行的实践,以生命圆满的教育为目的。掌握一个宗派的正见并能运用,具备一定的研究、弘法、教学或管理能力,目前设有唯识、中观、阿含、佛教制度等专业。
基础教育(本科·三年)
·本科三年课程设置
第一年、信仰与僧格养成
1、信仰建设:《佛陀及其圣弟子传》(十二周)、《佛法概论》(四周)、《高僧传》选读(四周)
2、《新戒比丘行护律仪》(三周)、(《以戒为师》?《行事钞》选读)(十二周)、《禅林宝训》(五周)
3、辅助课:古现代汉语、中医养身、佛门礼仪、梵呗
4、实践课:皈依共修、禅修、出坡、过堂、早晚课诵
第二年、道次第与菩提心
1、学习道次第:《菩提道次第略论》(十二周)、《印度佛教概论》(四周)、《百法明门论》(两周)
2、学习菩提心:《入菩萨行论》(十周)、《瑜伽菩萨戒》(四周)、《金刚经》(两周)、《因明入门》(三周)、寺院行政管理
3、辅助课:《心理学》、《西方哲学》、书法
4、实践课:皈依共修、禅修、出坡、过堂、早晚课诵
第三年、汉传佛教及重要经论
1、汉传佛教:《汉传佛教概论》(四周)
2、重要经论:《阿含概略》(十周)、《唯识三十论》(三周)、《十二门论》(四周)、
《六祖坛经》(三周)、弘法布教学(三周)
3、辅助课:西方宗教、宗教政策法规、论文写作、僧伽教务实习
4、实践课:皈依共修、禅修、出坡、过堂、早晚课诵
研修生教育(研究生·四年)
【唯识学专业】
一、专业课:
《菩提道次第略论》(半年)、《解深密经》(半年)、《瑜伽师地论·菩萨地》(半年)、《辨中边论》(半年)、《摄大乘论》(半年)、《集量论》(或<量理宝藏论>)(半年)、《成唯识论》(半年)
二、辅助课:
1、辅助课程:印度宗教哲学(半年)、国学经典选读(两年)、文献学(讲座)(两周)
内观禅修、空—大自在的微笑、华严五教止观、五家宗风、佛教教育学、传统养生、应用心理学、僧伽实务
注:国学经典包括四书、老子、庄子、易经、黄帝内经等。
2、讲座内容:佛教与心理治疗、现代物理学、太空科学、现代传播学、人力资源管理、法律、论文写作、佛教建筑艺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学
三、实践课:
菩提心的实践、禅修、传统养生、出坡、新式课诵
【阿含学专业】
一、专业课
《亲近释迦牟尼佛》(半年)、《阿含要略》(半年)、《阿含经》(一年)、《阿毗达磨俱舍论》(一年)、《清净道论》(半年)
二、公共辅助课
1、辅助课程:印度宗教哲学、国学经典选读、文献学(讲座)
菩提道次第止观章、华严五教止观、空—大自在的微笑、五家宗风
佛教教育学、传统养生、应用心理学
2、讲座内容:佛教与心理治疗、现代物理学与佛学、现代传播学、人力资源管理、法律、论文写作、佛教建筑艺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学
三、实践课
菩提心的实践、禅修、传统养生、出坡、新式课诵
【戒律学专业】
一、专业课:
《亲近释迦牟尼佛》、《四分律藏》、《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含注戒本》、《瑜伽菩萨戒》
二公共辅助课
1、辅助课程:印度宗教哲学、国学经典选读、文献学(讲座)菩提道次第止观章、华严五教止观、空—大自在的微笑、五家宗风
佛教教育学、传统养生、应用心理学
2、讲座内容:佛教与心理治疗、现代物理学与佛学、现代传播学、人力资源管理、法律、论文写作、佛教建筑艺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学
三、实践课:
菩提心的实践、禅修、传统养生、出坡、新式课诵
【中观学专业】
一、专业课
《菩提道次第略论》、《入菩萨行论》、《维摩诘经》、《大智度论》、《中论》、《入中论》、 《大乘玄论》(选读)、《肇论》
二、公共辅助课
1、辅助印度宗教哲学、国学经典选读、文献学(讲座)菩提道次第止观章、华严五教止观、空—大自在的微笑、五家宗风
佛教教育学、传统养生、应用心理学
2、讲座内容:佛教与心理治疗、现代物理学与佛学、现代传播学、人力资源管理、法律、论文写作、佛教建筑艺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学
三、实践课:
菩提心的实践、禅修、传统养生、出坡、新式课诵
(排版|荣卫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