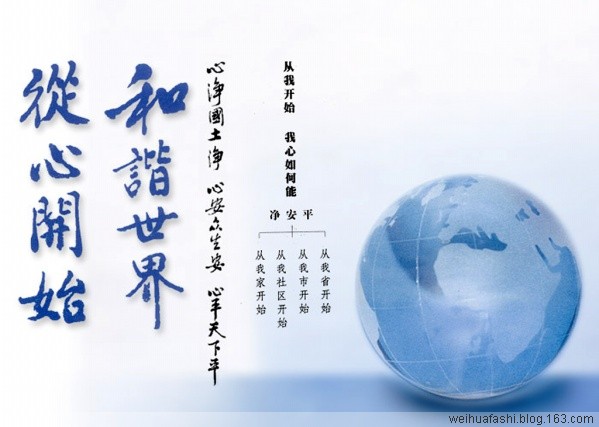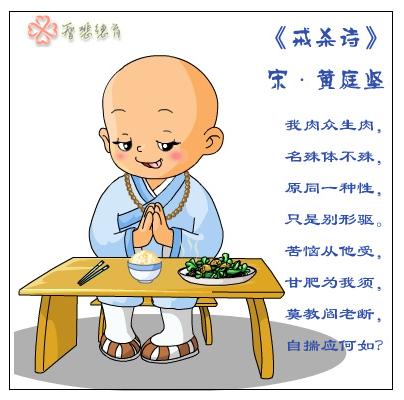善心的力量
堪忍尊者
只要不改变自己的心,
总是会有敌人伤害自己。
即使拥有比世间微尘还多的核子武器,
也无法去除自己及他人的妄念。
不但不能保证,反而只会带来伤害。
与善心相比,核子弹的力量是不足道的。
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全部重心,
都在心灵及善心的发展时,
加上每一个国民都接受这责任时,
成功才会到来。
向外寻求安乐是不可靠的,只会苦得筋疲力竭,而且永无止境,永无满足。
纵然仅运用大乘转念的一个技巧,也是最好的保证。例如,可运用一偈祈请文:
“至尊上师大悲者,如母众生恶障苦,今皆成熟于我身,我之善乐予他人,众生俱乐祈加持。”
遇到任何情况,仅运用这一偈祈请文,也将不断生起菩提心,舍己爱人。菩提心的修持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它给自己的保护远胜于几百劫生生世世学习空手道来保护自己。了悟菩提心是无可伦比的。
只要不改变自己的心,总会有敌人伤害自己。即使拥有比世间微尘总数还多的核子武器,也无法去除自己及他人的妄念;即使拥有如虚空般多的核武器,也没有意义。不但不能保证,反而只会带来伤害。与善心相比,这些核子弹的力量是完全不足道的。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有菩提心,我们就可以和枪、弹、军队及警察道别了。“一天一个苹果,可远离医生;一天一个善念,可远离敌人。”
如果一个国家全力发展心灵,以善心代替全力发展武器,将不会为其他国家所侵犯。如果一个国家的全部民众,都全力发展善心,会因为善心的力量,而没有被侵略的危险。
一个国家,不论军事力量发展得多么好,也没有把握永远击败它的敌人。若拥有大量军员及军备就表示永远会赢,是不合逻辑的。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全部重心,都在发展心灵及善心,且每个国民都接受这一责任时,成功才会到来。重心丧失,所有其他问题就接踵而来。
与其花费数以兆亿计的金钱于国防,不如将这些金钱用来提供大量公共设施,解决许多民生问题,让大家的生活安定舒适。
智者知道乐与苦全倚仗于心,在自心中寻求安乐,不假外求。心拥有全部安乐之因,在修持转念,特别是在运用苦于成就正觉时,你当明了这些。若忘记思维问题的利益——融合问题与大乘转念,且运用它们于大乘之道上——而只思维问题的短处时,将困难名为“问题”,于是就真的成为“问题”了。因此,是自己的心制造了问题。
这是用来解释问题的因何以是自心,问题如何源于自己的一种方法,这与思维问题的利益,运用它们于大乘之道上是相似的。当你止息厌恶问题的想法,建立喜欢它们的想法时,你的问题就真的变成有利、美好的事了。
任何感受到的安乐皆源于自心。从炙热时感受凉风带来的小乐趣,一直到成就正觉的大喜乐,每一份安乐都源于自心,由心所造。
所有因皆在自心中。既然心中的思维是安乐之因,那么就在心中寻求安乐。由自心中寻求安乐是佛法的基本要点,是佛陀的教法。而转念的修持是自心之最清晰、最善巧的寻求安乐方法。
自己的安乐并不仰仗于任何外在因素,即是否有人对自己恼怒,或批评自己。有人对自己生气时,如果还之以悲心,你会觉得他们是多么可怜。如果以慈心视之,就能温馨地对待他们,看他们的弱点。运用转念,会视他们为不可思议的珍贵,视之为自己生命中最可贵的人,比成千上万的金钱或堆积如山的钻石还可贵。在所有众生之中,他们是最可贵,最仁慈的。
不论某人如何以身、口、意,甚至故意伤害你,运用转念,你会觉得他们所作所为对自己发展心灵有无限利益。这种想法使自己非常快乐,并明了快乐源自于心,不是依于他人如何对待你或如何评价你。
自己认为的问题,源于自心;自己认为的快乐,也源于自己。自己的快乐不依任何外在的事物而定。愚者由外在寻求安乐,四处奔忙,忙忙碌碌地期待、追寻。如果由外在寻求安乐,不仅没有自由,也绝不会完全满足。无法看清任何事情,无法作出正确判断。而且,总是有许多问题,甚至有来自敌人及窝贼的危险,很难完全满意或成功。无论乌鸦由其嘴中亲自喂多少食物给杜鹃的雏,小杜鹃也不会变成乌鸦。同样,向外求安乐是没有保障的。唯一可确定的,是会苦得筋疲力竭,而这苦是永无满足且永无止境的。
也许这些教法对你没什么新意。然而,若能将此教法付诸实践,必能立即见到利益。若不能试着修持此法,纵然心中装满多如图书馆的转念教示,问题依然存在。大乘转念是将生命一切问题转化为安乐的最有效方法。尽可能实际修持此教法,才是最重要的。